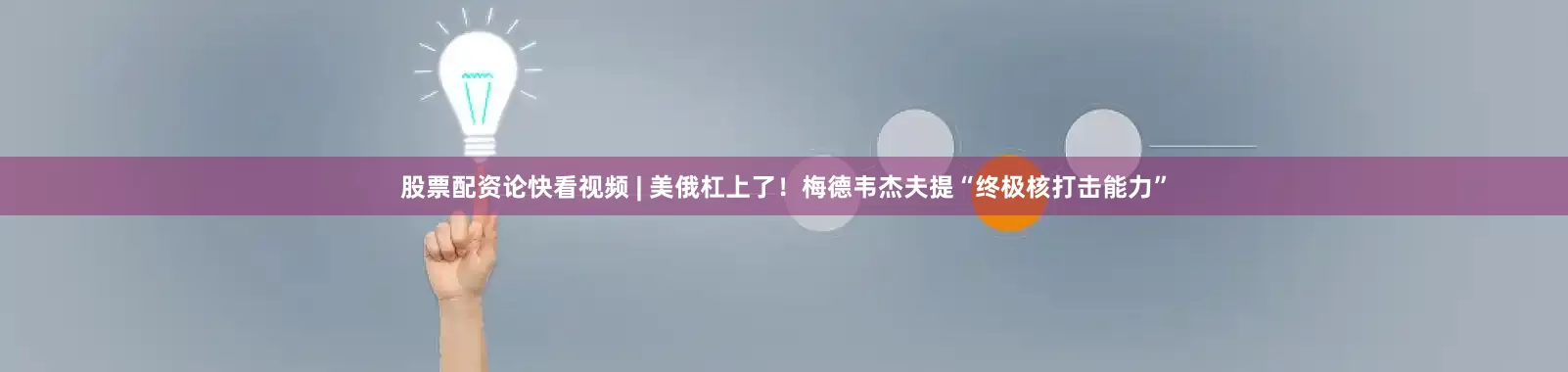▲2025年也是全球健康组织的融资年,但多个全球健康组织融资受挫,与此同时,全球公共卫生的警报正此起彼伏。(视觉中国 / 图)
“WHO的财务状况与其全球健康使命完全不相称,它的预算甚至比美国一个大型医院系统还要低,却被期望预防和控制大流行病、建设卫生系统,并应对日益严重的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危机。”
过去筹资年开筹资大会,有时候第一轮没有筹到应筹的数额,主办国大手一挥,关闭会场大门,号称不达数额不散会,“以后,恐怕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发行疫苗债券、大流行病债券,这些机制被认为有望为全球卫生带来急需的资金。不过,创新融资工具短期内难以替代作为主流资金来源的官方发展援助,只能作为补充。
“现在是全球卫生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确保WHO和其他全球健康组织拥有强劲的未来,这意味着更可持续和更具创新性的融资,这也意味着将来更少的资源(情况下),只能提高效率,专注于优先事项。”
文|南方周末记者 宋炳晨
责任编辑|曹海东
21亿美元——一架隐形战机的价格,或是全球烟草业年广告开支的四分之一,而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一年的全部预算。
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总部,2025年WHO年度会议上,总干事谭德塞的言辞中透露着无奈:“每年21亿美元的预算,对于一个承载着全球七十多亿人健康期望的组织而言,实在谈不上雄心勃勃。”
相比WHO最初计划,2026-2027双年度预算被削减21%,仅为4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2025年伊始,长期作为WHO最大捐助国的美国宣布将退出并中止资助。即便在预算缩水的情况下,仍有近19亿美元的缺口。
这种背景下,一场“瘦身”运动已经在WHO内部展开:助理总干事人数从12人减少到6人,总部各部门主任人数从70多人减少到34个人……一位接近WHO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基层组织的裁员方案尚在酝酿,但项目人员招聘已经全部暂停,差旅等相关经费也有收紧。
WHO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WHO正在对现有工作的优先级排序,确定哪些项目需要保留、缩减或终止,希望通过此举,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影响最大、优先级最高的项目上。
值得警惕的是,2025年也是全球健康组织的融资年,多个全球健康组织融资受挫。比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计划筹资119亿美元,这是一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推广儿童疫苗接种的国际组织,因美国拒绝继续提供资金,在6月融资会议上只筹集了90亿美元,这也是Gavi成立以来首次未实现融资目标。
与此同时,全球公共卫生的警报正此起彼伏:麻疹病例增多、百日咳复燃、猴痘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当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有力的健康卫士时,它们却被迫勒紧裤腰带。“多边主义和全球团结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美国乔治敦大学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主任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O. Gosti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预算甚至比不上美国一个大型医院”
这场席卷全球卫生领域的财政海啸,震中是美国的政治风向转变。2020年以来,美国对WHO的支持起伏不定。特朗普政府曾于2020年启动退出WHO程序并暂停资助,而后拜登总统上任后扭转了这一决定。
WHO数据显示,美国在2022-2023双年度仍是WHO的最大捐助国,贡献了12.8亿美元的会费和自愿捐款,约占该双年度全部捐助资金的六分之一。然而,2025年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又一次的“退群”宣言,打破了脆弱的稳定。
“美国一直在全球健康资金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的政治变化,意味着它从国际合作以及在科学、健康和疫苗领域的投资中回撤。”爱丁堡大学全球公共卫生项目主任黛维·斯里达尔(Devi Sridhar)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国际卫生合作持续倒退,并引发人们对疫苗和科学的怀疑。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5年援助预算可能会缩水高达17%。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与倡导总裁加吉·戈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不仅是数据变化,更是在财政压力和全球团结合作退潮的背景之下,捐助国政治意愿急剧转变的信号。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中心主任加文·亚米(Gavin Yamey)也观察到,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在内的多个主要捐助国都在削减其援助预算。
援助资金甚至在“隐性缩水”。例如,英国政府已将其国民总收入中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从法律规定的0.7%下调至0.3%。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主任汤胜蓝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过去十几年欧洲难民增多,安置难民经费原本由内政部门承担,但现在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将这笔开销算在对外援助款项中,“英国降至0.3%的援助中,实际上有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用于国内安置难民,这意味着真正用于海外的发展援助资金被大幅削减。”
转变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导致的国防开支激增,以及“美国优先”等国内政治议程的兴起。加文·亚米认为,这些都明确指向了“多边主义的退却”。
这种背景下,WHO现有的融资结构显得尤为脆弱。几十年来,WHO严重依赖少数高收入国家和大型基金会的自愿捐款,包括美国、英国政府,以及盖茨基金会。黛维·斯里达尔认为,这种模式使得WHO极易受到个别捐助方政策变动或财政困难的冲击,“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许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前全球卫生领域的核心矛盾,是“有限的资源与无限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世界银行在2019年估计,在全世界54个最贫困国家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一年的资金缺口为1760亿美元。新冠疫情后,发展中国家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本地化生产、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需求急剧增长且日益多样化,然而需求激增的同时,来自传统捐助国的资金却在萎缩,这使得资金的“供需鸿沟”愈发突出。“这也给了政客借口,既然增加多少资金都无法满足,那不如将资金用于本国民生。”
“WHO的财务状况与其全球健康使命完全不相称,它的预算甚至比美国一个大型医院系统还要低,却被期望预防和控制大流行病、建设卫生系统,并应对日益严重的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危机。”劳伦斯·戈斯汀还担任WHO卫生法合作中心主任,他认为,WHO的财务状况“无疑是不足且不可持续的”,这场由美国“退群”点燃的导火索,引爆了一个早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
当资金减少,WHO则只能被迫“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不论我是否支持这一观点,鉴于目前的资金状况,世卫组织别无选择。”加文·亚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5年5月,谭德塞宣布将“在不断变化和支离破碎的全球卫生格局中保护和改革世卫组织”,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指南数量、合并职能、优化成本,并合并、迁移、缩减和停止一些规划,进行裁员。
一直以来,因为资金利用效率不高,WHO备受批评。许铭表示,主要问题是受援助国家“吸收率”低——即资金中真正落实到项目并投入使用的比例不高。例如有的国家在不断要钱,实际上去年和前年的钱还没有用完;而有的国家面临相似问题,却拿不到太多资金,分配不均。
汤胜蓝曾在WHO总部和国家办公室拥有多年工作经验,他认为,谭德塞的改革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错失了解决关键问题的良机——重组世卫组织支离破碎的治理结构。
事实上,WHO由日内瓦总部和6个“半独立”的区域办事处构成,区域负责人由其区域内的成员国选举产生,对该区域内成员国负责,而非直接对日内瓦总部负责,谭德塞设计的改革也集中在WHO日内瓦总部。汤胜蓝认为,这种“六个婆婆”式的管理架构,既不符合管理逻辑,也影响了组织的效率和一致性。
在区域办事处之下还有国家办公室。“许多设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办公室没有太大存在必要,它们除了在会议上致辞或制定一些因缺乏足够经费而从未有效执行的国家健康/卫生战略外,并未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汤胜蓝观察到,很多国家办公室的预算在支付完工资后,已所剩无几。他认为,除了中东一些富裕但缺乏技术能力的国家之外,多数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国家的WHO代表处存在的必要性不大。
作为世卫组织改革的一部分,WHO宣称将会减少制定指南的数量,但会提升质量和可用性。但是,这些指南或专家共识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许多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常遵循指南制定卫生政策,减少指南的制定,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事实上,这些指南绝大多数并非由WHO的职员撰写,而是通过召集全球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完成,一份中大型指南的开发成本为几十万美元。“这些钱对于世卫来说不算什么,但对非洲国家卫生部来说就是一个大钱,关掉一个不必要的国家办公室所节省的数百万美元,足以资助好几个专家委员会,产出多份高质量的指南。如果专家委员会通过线上工作,减少线下会议,也可以降低因国际旅行带来的费用。”汤胜蓝说。
另一个困境在于人才。近几年,WHO在招聘高水平专家时面临着来自全球基金、Gavi等众多国际组织的激烈竞争。汤胜蓝认为,WHO基于成员国地域平衡而非纯粹择优录取的招聘原则,有时也难以保证招到最合适的人才,预算危机无疑将加剧“用人荒”。
WHO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改革的核心焦点之一是确保在国家层面的行动保持强劲并得到加强。劳伦斯·戈斯汀建议,在当下,WHO应当聚焦核心优先事项,提高效率,尤其应关注非传染性疾病、伤害和精神健康等主要疾病负担。
筹资一次花几年,变为一直在筹资
传统捐助体系失灵,WHO正竭力开辟新的“水源”。
最核心的变革,是增加评定会费在总预算中的比重。评定会费,即成员国根据其经济和人口规模缴纳“会员费”,这部分资金灵活、可预测,不受捐助方指定用途的限制,被视为世卫组织资金的“压舱石”。
在2025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成员国连续第二年批准了将会费提高20%的决议。此举旨在将评定会费占核心预算的比例从几年前的约16%提升至接近40%,最终目标达到50%,从而降低对少数捐助方自愿捐款的过度依赖。加文·亚米认为,这些增幅表明,成员国显然对WHO的可持续资金筹措感到担忧。
一位在国际组织参与筹资工作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筹资工作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国家作为“主办国”统筹,在过去,筹资年开筹资大会,就是主办国彰显魄力的时刻,有时候第一轮没有筹到应筹的数额,主办国大手一挥,关闭会场大门,号称不达数额不散会,“以后,恐怕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许铭认为,未来更有可能的是,筹资年将变为“筹资季”,从筹资一次花几年,变为一直在筹资。Gavi发言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筹资活动结束以后,他们正在积极与尚未承诺捐款的捐助方接洽,其中一些捐助方也在自己的预算中作努力,现在他们的重点仍然是调动剩余资金,确保未来五年工作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融资方式也在显现。加吉·戈什强调,更加审慎地运用新的融资来源至关重要,私营资本、慈善资金以及混合融资都在发展议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要真正发挥这些资金的影响力,还需要依托稳健的制度架构、透明的治理机制、明确的投资机会,以及能够真正惠及双方的风险控制工具。
2020年,WHO基金会成立,旨在为公众、个人大额捐助者和企业合作伙伴提供一个直接支持WHO的平台。2024年5月,WHO发起“投资回合”(Investment Round),旨在从更广泛的捐助方(包括新兴经济体、基金会和私营部门)为WHO在2025-2028年的核心工作筹集可预测和灵活资金。截至2024年5月20日,该倡议已获得19.7亿美元的认捐。
利用金融工具则是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领域。发行疫苗债券、大流行病债券,这些机制被认为有望为全球卫生带来急需的资金。Gavi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通过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将赠款与低息贷款相结合,使国家能够投资于自己的疫苗接种项目和卫生基础设施。
不过,效果还需评估。许铭发现,这类工具目前体量有限,例如“债转卫生”项目,通过债权国适当放弃其未被偿还债务,用于债务国自身的卫生体系建设,该项目从2007年推出第一个债转项目以来,至今累计盘活的资金仅3亿多美元,与巨大的资金缺口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他强调,创新融资工具短期内难以替代作为主流资金来源的官方发展援助,只能作为补充。黛维·斯里达尔的团队也研究发现,大流行病债券等机制并未兑现其承诺。
在外部筹资挑战重重之际,一些区域和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内部,强调自主和国内资源动员。在非洲,卫生部门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危机,官方发展援助在2021年至2025年间急剧下降了70%,2025年4月,非洲疾控中心Yap Boum博士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介绍,他们融资的三大支柱中,第一个就是动员更多的国内资金,其他两个是创新融资和开拓私营部门。
“我认为,鉴于全球面临的风险,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为全球卫生安全贡献公共资金。”加文·亚米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3日,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的旗帜在风中飘扬。世卫组织总干事在4月22日表示,美国的预算削减使得联合国机构的财务状况处于负面,迫使其减少运营并裁减员工。(视觉中国 / 图)
全球健康未来,谁将替代美国?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就是WHO等全球健康组织如今的窘境。
资金的短缺最终会转化为行动的迟缓和生命的代价。世卫组织等全球健康组织的预算危机,不仅仅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更预示着一个更脆弱、更割裂的全球健康未来。
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疾病监测和应急响应上。历史上,美国为WHO的应急和防范工作以及核心项目分别资助了约20%和25%的资金。多个由美国疾控中心(CDC)支持、针对疫苗接种和疫情监测的技术部署项目已被冻结,直接影响了在非洲等多地的疾病监测和免疫支持工作。
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全球多边主义合作精神的衰退。劳伦斯·戈斯汀的看法悲观,“特朗普政府几乎终止了美国对低收入国家的全球卫生援助,要为全球卫生资金的崩溃负很大责任。”他认为,在富裕国家正在将财政资源优先用于国内事务或国防开支时,那些有能力承担更多资金的国家则需要做出更多努力。Gavi发言人也提到,印度尼西亚这个曾经的受援国,已经承诺向Gavi捐款3000万美元,实现了向捐助国的转变。
现实是,即便是OECD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增加了对WHO的捐助,也很难填补美国留下的窟窿。新兴经济体能否完全填补资金缺口,多位采访对象都保持着谨慎态度。
许铭预测,未来不太可能由某一个国家替代美国扮演的角色,而是会进入一个由“多个利益攸关方”集体发挥作用的时代。他解释,这包括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如NGO、慈善基金会和私营部门)以及国际组织,它们将“针对不同利益,采取协同行动”。这预示着一个更加去中心化,但也可能更加碎片化的治理模式。
由于全球层面的资金和领导力变得不再可靠,非洲疾控中心等区域性机构正积极推动区域内的自主性。推动疫苗和药品的“本地化生产”,加强各国的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建设,这些都是在为减少对外部依赖、增强自身抵御风险能力而布局。
对此,WHO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当前的危机是各国“从过度依赖援助转向在调动卫生资源方面实现自我可持续”的一个机会。
然而,这个看似“多元”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有区域力量在崛起,但并非所有地区都有同样的能力和资源。治理的碎片化可能导致协调困难、标准不一和资源分配不均,使那些地缘政治上不占优势、自身能力又弱的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
当然,未来并非一片灰暗。加文·亚米也看到了积极的信号,他认为,成员国签署大流行协定、同意增加评定会费等举动,是“向多边主义倾斜,而非退却”的表现。这说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国际社会依然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现在是全球卫生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确保WHO和其他全球健康组织拥有强劲的未来,这意味着更可持续和更具创新性的融资,这也意味着将来更少的资源(情况下),只能提高效率,专注于优先事项。”劳伦斯·戈斯汀说。
恒正网-恒正网官网-配资网站大全-十大合法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配资网站很多事发生的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 下一篇:没有了